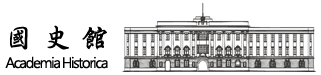【國史館研討會第一天新聞稿】《蔣中正日記》(1937-1947年)新書發表座談會
國史館於2025年8月15日(星期五)下午2時假臺北館區四樓大禮堂,舉行《蔣中正日記》(1937-1947年)新書發表座談會,與會貴賓有前總統府資政胡為真、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呂芳上、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藍士博、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主任游惠容等蒞臨。
國史館陳儀深館長在開幕致詞時表示,國史館為紀念終戰八十週年,特別舉辦三種類型的紀念活動,包括本館與臺灣文獻館合辦的六場系列講座,其次是從8月15日開始為期三天的「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」學術研討會,以及「亮光與暗影:1945年前後的臺灣重要史料微型展」,目的是希望全面地回顧與省思此一關鍵年代的歷史,另出版兩蔣日記是國史館這兩年的既定工作,此次出版的蔣中正1937至1947年日記,恰好涵蓋中日戰爭8年及戰後2年,與此次研討會的時間斷限相吻合,納入本次活動更能相得益彰。
這次邀請主題演講的貴賓是潘佐夫(Alexander V. Pantsov)教授,其大作《蔣介石:失敗的勝利者(Victorious in Defeat)》除了充分使用俄文和英文檔案,更大量引述蔣中正日記,充分呈現研究的廣度和深度,足以證明日記在歷史研究的重要性。
這幾天國史館紀念活動的消息見報後,立刻有某些特定人士批評使用「終戰」是一種媚日的態度,不直接使用「抗戰勝利」,是在迴避或曲解歷史。這樣只看標題就攻擊,雖然反映了社會分歧、政治對立的現實,但卻是不必要、也是不公平的過度解讀。個人在8月7日第一場系列演講致詞時,曾以自身生命經驗為例,家父是雲林鄉下的農夫,日治時期曾去南洋當軍伕,因眼疾提早回臺,林內鄉多位軍伕沒這麼幸運、死在南洋;在成長過程中,常聽到家父使用「日人時代」、「降伏(こうふく)」以後如何,起初以為他講的和學校講的一樣是「光復」,因為發音類似,事實上「降伏」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說話、「光復」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說話,這是生命經驗不同使然,應該互相尊重。何況「終戰」字面意義就是戰爭結束,具有中性的意涵。
回顧歷史,日軍發動侵華戰爭的藉口之一是「反共」,結果不但使得蔣中正停止剿共、必須與中共合作抗日,而中共藉著八年抗戰壯大,進而在戰後國共內戰獲勝,日本侵略中國造就了一個共產中國的誕生,實在是歷史的一大諷刺。另一方面,蔣中正領導全面抗戰,應邀參加開羅會議,最後與美英蘇同盟打敗日本,參與創立聯合國成為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,這些事蹟在中國歷史的角度而言,當然是重要功業,不容抹煞。然而在2025年的臺灣,回顧1945年的鉅變,更應有多元的角度重新反思。
〈亮光與暗影:1945年前後的臺灣重要史料微型展〉就是想要回應此一議題,當時臺灣不少知識分子因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而歡迎祖國,卻因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不當、治理失能,不到一年半就發生二二八事變,展覽中挑選林獻堂,王添灯和吳新榮的日記為例,可以作為時代變化的見證; 1991年史丹佛大學出版第一本研究二二八的專書以《悲劇性的開端》為書名,這個開端包括美國方面基於開羅宣言的承諾,協助國軍占領臺灣,有一種共管的態勢,這也是美國政府為何在二二八事件中作壁上觀的原因,必須到1949年末、尤其1950年初韓戰爆發,美國才改變立場,透過舊金山和平條約對臺澎地位做了特殊的處理。這次的「重要史料微型展」是要呈現臺灣1945的複雜性,避免一廂情願的單方說法,想要呈現的不只是國府的觀點,還包括美國的、英國的、日本的以及具代表性的臺灣人菁英的觀點。其中有一份特別的史料,即1975年王育德先生有感於匿居印尼山林三十年的臺籍日本兵返臺後,沒有受到臺日雙方政府應有的重視,而成立「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」,透過法律的政治的社會運動的手段,奮鬥了12年才獲日本國會通過每人兩百萬日圓弔慰金的補償,王育德已於1985年去世,其兄王育霖律師就是臺南228的受難者。我們要尋求以臺灣為主體的戰後史觀,就不能不注意這樣的事件。
接著是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人文學院潘佐夫(Alexander Pantsov)教授的主題演講〈1937-1947年的蔣中正與史達林的關係:《蔣中正日記》的新啓示〉,蔣中正日記清楚地記錄了他對這位蘇俄領導人前後態度的演變,蔣中正的兩難處境在於一方面基於愛國心對史達林「赤色帝國主義」的憎惡情緒,另一方面則是與強敵作戰的殘酷現實,史達林提供實質援助,並有可能參戰解圍。蔣中正既向史達林求助,對其表示感謝與頌揚,又竭力維護國家尊嚴,不斷徘徊於自卑與自尊之間。1939年秋,史達林選擇與德國同一陣線並接近日本,使蔣非常惱火,日記顯示蔣對史達林的態度開始惡化,並因中共的活動而加劇,1941年至1944年蔣對這位蘇俄領導人侵犯中國新疆領土完整的行為,表達嚴厲批判。從1944年起,他一直試圖說服美國人不要信任史達林。1945年的《雅爾達協定》及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的簽署,使蔣中正對史達林心生厭惡,隨著1946年春蘇俄自東北撤軍及國共內戰的爆發,蔣對蘇俄的憎惡情緒達到頂峰。在蔣看來,史達林統治下的蘇俄,如今與戰時的日本並無二致,蔣的日記清楚地反映了其心路歷程的轉變。
隨後播放紀錄片《破曉時分:抗戰勝利與受降》精華剪輯,該片由國史館製作,聚焦於1945年9月至10月從密蘇里艦、南京到臺北等三場受降典禮的紀錄片。並同步於402會議室展出「亮光與暗影:1945年前後的臺灣重要史料微型展」。接下來是國史館為慶祝「歷任總統資料庫」使用人次破百萬留言回饋活動頒獎典禮,「歷任總統資料庫」為本館與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、李登輝基金會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合作,將蔣經國與李登輝總統相關檔案文物,以時間為主軸,結合出版品、日記、講詞等文本整合呈現的資料庫。自2022年1月19日上線開放,至2025年5月初以來,使用人次已突破百萬人,為鼓勵新、舊使用者的持續關注與支持,特別舉辦這次留言徵件回饋活動。
接著是新書座談會,與談人劉維開教授表示,十年前曾有民間單位以蔣中正日記抄件,完成一份抗戰八年日記的文字檔,提供學界應用,但缺乏原件的比對,國史館作為兩蔣日記的保管機關,應用原件出版1937至1947年蔣中正日記,對於研究抗戰史或戰後臺灣史是莫大助益,在閱讀後提出幾點心得分享:一、和戰抉擇和蔣的冒險性格。1937年11月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時,轉達日本的和平條件,當時國防最高會議多數人都傾向接受,只有蔣中正不同意,以為「此時求和乃為降服,而非和議也」。蔣本身冒險性格甚強,對日作戰有著「非死即生」的認知。二、持久戰略的提出。雖然蔣在1937年上半年,尚未預料戰事爆發,但從盧溝橋事變、八一三淞滬戰役到南京保衛戰,他認為打敗日軍必定是長期的持久戰,在空間要謀求國際干預,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。三、蔣對南京保衛戰的態度。蔣明知南京不能守,但不能不守,這是對國家軍民的一個交代。所以許多機關已遷至武漢或重慶,蔣則堅持留在南京,他認為多留一天,是跟人民、軍隊一起站在前線抵抗侵略。四、1944年是蔣最痛苦的一年。除了面對日軍一號作戰攻勢,還要面對羅斯福來電要求由史迪威指揮中國所有軍隊,美方揚言如不照辦,將斷絕軍援,這是蔣最痛苦,也是情勢最岌岌可危的一刻,但都在他的堅持下,迎來最終的勝利。
薛化元教授則對蔣中正日記的出版亦憂亦喜,喜的是這是研究民國史、戰後臺灣史的重要史料,憂的是蔣中正常將個人情緒帶入日記,會影響研究者的解讀。以陳誠為例,如果光看日記記載,從蔣對陳誠的痛斥程度,是無法理解他為何重用陳誠。閱讀蔣日記應時時保持警覺,從個人研究興趣得出的感想:一、二二八事件前夕,蔣在1946年底來臺,感受不到情勢不穩的氛圍,在事件發生當下,他第一反應這些人不是共產黨,這個反應較接近事實。二、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擬定憲法草案12項原則,蔣的態度原本抱持國民大會「採納」,而非「接受」。到了制憲大會遭到中共及民主同盟抵制,過去我們以為是雷震從中穿針引線和協調,但從日記來看,蔣中正為了獲得青年黨、民社黨的支持,頻頻與張君勱見面商討憲法草案,然而制憲國大的代表不少是戰前選出,有意回復五五憲草,這讓蔣中正非常苦惱,甚至明確表達不採納五五憲草,要以政協憲草為準,對國民大會頻頻想要擴權,蔣也十分苦惱。再就地方自治的法源依據,行政院起草卻又攔置,對照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的總裁批簽,發現蔣中正有意儘速完成立法,為何後來遲遲不能進行,直至1994年才真正立法,這是值得開發和研究的議題。
黃自進教授則從外交的角度解讀日記,提到戰後日本於1951年召開日本外交總檢討,認為日本戰敗的悲劇起點是日本退出國際聯盟,與國際社會隔絕,日本學界認為日本戰敗根源於九一八事變,造成政黨政治瓦解,喪失與英、美和解企機,最終引發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。而蔣中正面對中日戰爭的危局,最大的貢獻是堅守與英、美同一陣營。但蔣中正也面臨國內的挑戰,第一次的挑戰是戰爭初期,中國內部存在和戰之爭,在陶德曼調停下,蔣中正獨排眾議,不接受日本的停戰條件,因為接受的條件即是與日、德的「防共條約」,將會喪失蘇聯給中國的援助。第二次的挑戰是法國投降,滇越路與滇緬路相繼關閉,中國軍援路線遭到斷絕。此刻國內又重提改善與德國的關係,若中國向德國靠近,將會失去日後與英、美結盟的可能性。簡言之,蔣中正雖受黨內同仁的挑戰,但堅決與主流國際社會同一陣營。蔣中正最大貢獻是戰時與美國結盟,最大的失敗也是戰後與美國失和,導致最終在大陸的潰敗。
最後一位與談人是陳翠蓮教授,蔣中正1937到1947年的日記中,提到臺灣的次數極少。直到日本投降後,蔣中正才對臺灣產生初步構想,他將臺灣定位為中國東南的門戶及國防基地。然而,隨著國共內戰情勢變化,這個構想未能實現。蔣在日記中對臺灣的描寫有兩個高峰。第一次是在1946年10月,他首次來臺巡視。當時中國內戰動盪,但臺灣在他眼中卻有如「世外桃源」,讓他在國事如麻的情況下得以喘息,他對民眾的熱烈歡迎感到高興,並認為臺灣「尚無共黨細胞」,猶如「一片淨土」,應將其建設成「全中國的模範」。他讚嘆臺灣風光秀麗,也佩服日本的建設,認為收復臺灣讓八年抗戰的苦鬥有了價值。然而,在這次巡視中,他做了一個關鍵決定,將原本駐紮臺灣的第70師調回中國內戰,使得臺灣兵力銳減,為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伏筆。第二次高峰是二二八事件。蔣中正對事件的看法,反映了他與臺灣現實的落差。他得知事變後,第一時間寫下「臺灣暴民趁國軍離臺、政府立足未穩…發動暴動」,可見他認為事變主因是軍隊被調走,而非治理問題。他後續的決策都圍繞著增派軍隊、訴諸武力鎮壓,及抱怨陳儀「疏忽無備」與「沒有及時報告」,而非治臺不當。他認為陳儀處理不力,導致事態擴大,雖撤換陳儀,但並未對其懲處,總結來說,蔣中正因國內情勢緊急,其處理方式是訴諸武力,他對臺灣的治理理解明顯存在落差。陳儀深館長在座談會最後預告明後兩天還有24篇論文發表,相信可以客觀呈現臺灣學術界在這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,歡迎踴躍參加。
新聞聯絡人:林科長(02)2316-1062

圖二、潘佐夫教授進行主題演講

圖三、「歷任總統資料庫」使用人次破百萬留言回饋活動頒獎典禮

圖四、新書座談會(左起黃自進教授、陳翠蓮教授、陳儀深館長、薛化元教授、劉維開教授)

圖五、新書座談會合影(左起黃自進教授、陳翠蓮教授、陳儀深館長、薛化元教授、劉維開教授)